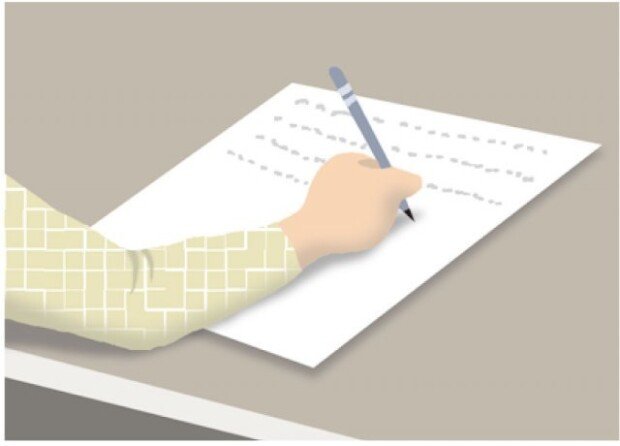

“我們成了作家。我們堅韌執著地寫作,從不失去對寫作的信心。”——雅歌塔·克裏斯多夫《文盲》
語言和思考是有機的。說話的方式一改變,思考的方式自然也會不一樣。21歲前往法國,在那裏生活了18年,才有了這種感悟。用外語寫作的我和用韓語寫作的我,思考的方式不同。
支配我的語言和思想的外語,我把它叫做母語之外的語言。這種語言與母語產生沖突,放慢思維速度,只挑選能說的話而不是想說的話來寫。我因為那種語言而成了一個完全無法屬於任何地方的局外人。
雅歌塔·克裏斯多夫受匈牙利革命的影響,離開祖國到瑞士避難,她在諾沙特爾的鐘表工廠工作時學習了法語,是一名用外語寫作的作家。她用一句話就毫不苦惱地概括了歷史和個人的不幸,以及一個人超越不幸的壯闊人生和業績。這種自然的語言有時讓人覺得野蠻。
即便如此也能做些什麽的人,不是在和“即便如此”這個詞之前附加的條件鬥爭中獲勝的人,而是堅信自己不會輸的人。這種信心之中,必須要有時間在一張白紙上結結巴巴地一行一行寫滿。語言的欲望在貧窮的語言面前下跪的時間,為了語言的本質脫去修飾的時間。這一信心中,有懇切的文盲的時間。克裏斯多夫和她的作品對我來說,不是夢而是信心。我相信作家的話:“我們堅韌執著地寫作,從不失去對寫作的信心。”再一次,回想起我母語之外的語言,記錄下我的信心。“寫作。”這種信心中,既不需要過去型也不需要未來型。







